属兔的和属什么的婚配,75年属兔47岁有一灾
2024-05-06
更新时间:2024-05-07 00:03:15作者:佚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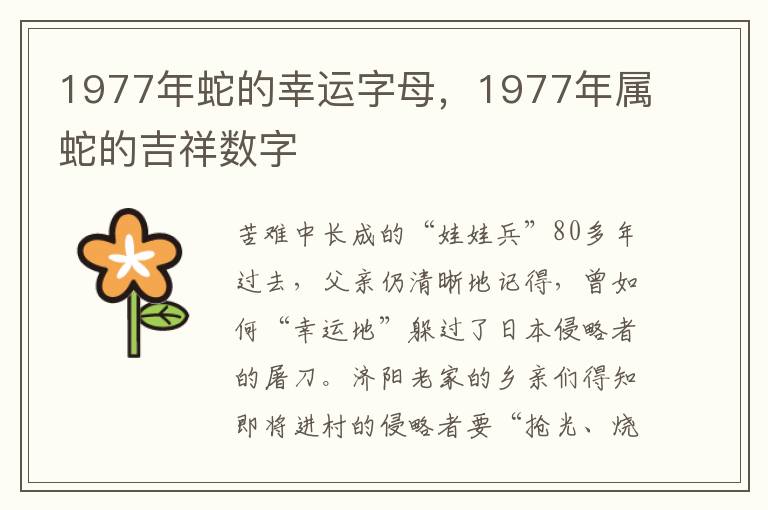
每每讲到从前,父亲总会习惯性地带上一句:“我还真是幸运啊。”比如他说:“按农历算,我出生在1932年的九月初二。后来一查,对应的日子刚好是阳历的10月1日,国庆节。哈哈是不是很巧?我还真是幸运啊。”
苦难中长成的“娃娃兵”
80多年过去,父亲仍清晰地记得,曾如何“幸运地”躲过了日本侵略者的屠刀。
那是1937年冬的一天,日军侵入山东。济阳老家的乡亲们得知即将进村的侵略者要“抢光、烧光、杀光”,集体向野外奔逃。为保性命,一些实在跑不动路的老幼病残被无奈留下。日本兵破门而入时,年仅5岁的父亲并不知发生了什么,只是无措地 在地上,大睁着眼睛,仰脸看着日本兵在他头顶上“嗖”地抽出了刺刀……炕上,还睡着他不到2岁的小妹妹,我的姑姑。恍惚间,旁边的中国翻译似摆摆手说了些什么,日本兵缓了缓,收刀离去。
父亲也记得,那时候,每当侵略者的飞机轰隆隆飞过老家的上空,我的爷爷都会赶紧关闭家里的木门,拉着他跪下。爷爷并不知道那是飞机,他强按着父亲的头往地上磕着,不住地祈求。后来,刚满12岁的父亲,就被迫在拿着刀枪棍棒的日伪军监督下,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铁锹和村里的一些人去修炮楼,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父亲14岁时,我的奶奶病逝,原本就贫穷的家又缺失了应有的照管,日子过得更是雪上加霜。可是,再难的日子也得过下去。他找来别人不要的碎旧布头,熬了浆水打成袼褙;野地里拔些苘麻用水浸泡,剥出来搓成麻绳;然后,穿针引线纳鞋底,依葫芦画瓢地给自己和家人做鞋穿。看到木匠用墨斗排线,他反复琢磨、尝试,竟也做出了一模一样的墨斗。最酷的,是他曾花了好几天的工夫,做出过一辆特别好用的棉纺车,以至于我的太爷兴高采烈地扛去送给了他已嫁到外村的闺女——父亲的姑姑。村里人都说:这何伙子,心可灵啊!父亲的曾用名是何其福,何伙子是他年少时的乳名。父亲有个会拉胡琴的远房哥哥,见他喜欢胡琴,就给了他几根弦;父亲便用竹子和空罐头盒自制了琴弓和琴筒——没有蟒皮蒙琴筒,就用猪膀胱膜代替。接下来,在没有乐谱且无人指点的情况下,竟吱吱呀呀兀自拉响了属于自己的乐曲。
“心可灵”的父亲,总是不断琢磨,见什么就学什么,做出的物件用着顺手,通常会被乡亲们拿去,而后回报给他几个热热乎乎的高粱饼子。
父亲还记得,1946年,从济南调了两个团和的队伍对打了整整一个昼夜,之后大获全胜的队伍驻进了济阳县城。有趣的是,乡亲们后来发现,他们的县长原来就是之前在村口乔装成卖油条的伙计的地下党员。
1947年~1948年的土动,让解放区里每一户农民都分得了田地。而那时,战火纷飞的前线亟需扩充队伍,壮大力量。“保家、保田、保饭碗”——实实在在的口号,鼓荡着有志青年们的心;村头巷尾,满是“妻送郎,父送子,杀敌上战场”的热烈场景。父亲瞒着家人悄悄报了名,直到征兵的队伍要出发,我的爷爷才从乡亲们口中得知“你家何伙子要去打仗了”。那一次,全村一起出去的6个青年里,更大的23岁;父亲16岁,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娃娃兵”时的父亲。( 提供)
父亲说,那是1948年底的一天,征兵处的干部将他们整个地区前来参军的一百多人,集中在邻近的韩家村,吃了一顿热闹非凡的“大餐”。“一大桌子人坐下来一起吃,吃得相当好。”他说着,眼睛里闪动着年轻人才会有的欣悦和。饭后,队伍。准备出发时, 在房顶上的地方干部往远处扔了几颗手榴弹——震耳的爆炸声是更高的欢送仪式。就在那个非常有意思的特定场合下,父亲告别了家乡和亲人,踏上了完全未知却满心期待的征程。
战火中速成的员
饭后他们马不停蹄,一直走到已经是老解放区临沂县一个叫张辛庄的新兵训练地,被编入渤海二军分区特务连。天已黑透,走得太久的父亲,两条腿已经完全不听使唤。
摸黑领到一套土布棉衣裤的军装,一双棉布鞋和一条轻薄的小棉被,还有一个底部有环可拴在腰间的搪瓷碗和一双筷子,皮带是后来才发的。“这全部的家当,南下时我一直背到了上海。”父亲说,宿营就在老乡家,他们铺了麦草在地上就寝。一个屋子里的新兵们都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军装,就着蜡烛,互相看着自己变成军人的模样。
第二天训练开始,百十多人的新兵连队,父亲仍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未成年的他还没有发育完全,小小的个子只能排在队尾。完全按照实战要求的训练是艰苦的——之前如散沙般,连“立正、稍息”都不知道的一群农民,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达标,投入战场。谁也没有想到,他们之中最小的那个、连成人尺寸的军装都穿不起来的娃娃兵,会在训练中爆发出空前的能量。1949年初完成训练时,意志坚定、机智勇猛的父亲荣立二等功,被野战军33军99师197团一营机炮连连长挑去当了通讯员。同村其他5名跟父亲一起受训的青年,统一分配在一连,他们成了不同连队共同抗敌的战友。
进入战斗部队,父亲在数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中迅速成长起来。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从江苏江阴到江西湖口,一路铺开的百万雄师,一声号令浩浩荡荡地开过江去。父亲说,那是他经历的之一场特大战役。前一晚,一艘艘乘载几十人的大木船,便已全部隐在了岸边的苇丛中。他们所在连队的出发地点是安徽的马鞍山。正是南方的梅雨季,黝黑黏湿的夜晚,细雨早已浸透了身上的衣服。为了辨识,他们每人戴一只正反面红白两色的袖箍,以便昼夜翻转。没有表,亦不知隐蔽了多少个时辰,不远处闪过裹着红布的手电筒明暗交替的信号。那一刻所有的木船驶出苇丛,暗夜里只听得艄公奋力摇撸,和战士们以锹做桨划水的“啪啦”声。到对岸时天色依然昏暗,他们只能先伏在麦垄里观察敌情。蒙蒙亮时,同样潜伏在麦田里的兵发现了他们,双方开始正面交战。
我问父亲:你有紧张和害怕过吗?毕竟是生死战斗……哪里顾得上害怕!父亲笑我们边打边追,他们边跑边退——兵败如山倒,人心涣散的兵早没了士气!那一次,他们沿着公路向前,整个打乱了的队伍。说到这里,父亲讲了个小插曲:打到泗安镇时,他们找到一户农家,在院子里铺了麦草暂做小憩。刚刚安顿下来,就见一个挑着担子的年轻人走进院子。有个眼尖的老兵一声惊呼:这不是一班长吗?原来,他们小憩的这户农家,正是这个从队伍俘虏过来、因表现不错还担任过他们“一班长”、后来又趁乱逃跑了的年轻人岳父母的家。巧的是他过来走亲戚,歪打正着,再次成了俘虏。“那些没有信仰的人怕苦怕累更怕死,哪里会有坚定的立场?”父亲手一挥,结束了这个故事。当我说起影视剧中,曾看到过战争中的千辛万苦时,父亲顿了下,讲了另一个小插曲。
也是那次的渡江战役,很长时间没有喝到一口水的父亲口渴难耐,交战中又不可能停下来找水。于是,在清晨渐明渐暗的熹微里,当他隐约感觉到路边有个小水窝亮了下,便赶紧俯身用系在腰间的瓷碗舀起来喝了一口。而那一口臭出天际的味道,几乎翻转了他的五脏六腑——那是农民浇地的粪汤……可是他依然没有机会去找一口能够漱嘴的水。枪林弹雨中的父亲,必须全速前进。追敌途中,父亲看见过在农田里已经泡发的敌尸体,也看见过血流满面、坐在路边哭泣的敌伤兵,他们跟他一样年轻。可是他顾不上多看一眼,更没时间去想什么——他不能停下脚步。没有见到过父亲战斗中是怎样一副装备,我只能从他的简述中想象着他当年的模样:背包里那条轻薄的小棉被,腰间那只吃饭喝水于一体的搪瓷碗,右肩左斜的子弹袋和左肩右斜的干粮袋。停下来吃饭的时间是没有的,饿了,抓一把炒米塞嘴里嚼嚼就好;渴了,就全凭运气了。永不离身的是那条高过他的三八大盖,扛着、举着、端着……战争的苦难,影视剧里没办法一一还原;父辈们的艰辛,又岂能点点滴滴具体、精准地展现?
陆军时的父亲。( 提供)
即便如此,父亲依然笑哈哈地说,行进途中,曾有一次路过济南桑梓店,远远地看到几盏明晃晃不凡的光亮,队伍里见过世面的老通讯员悄悄告诉他,那就是中的电灯。而那时候,电灯还是个稀罕物。“我还真是幸运啊。”父亲说着,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笑纹里,也透露出不凡的光亮。再往前,到了一个车 ,他竟意外地见到了老辈们说过的火车,虽然那只是个并没跑起来的拉煤用的车盘子。“若不是出来了,我怎么看得到这些,又怎么可能坐上大木船呢?”
就这样,跟随部队一路南下的父亲,边打边进,到了苏州,又到了上海。说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父亲所在的连队攻到上海城边,远远便见敌方林立的炮楼和哨卡。他们白天蛰伏,夜间则趁敌不备悄无声息近前搞“破坏”——那些用削尖的竹子围起的军事掩体,都被他们拆得七零八落,抽走当做饭的柴火烧掉了。有天夜里,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刚退进挖好的隐身工事,忽在坑边拽下了几个圆圆小小、湿漉漉的不明果实。口干舌燥的父亲一把扔进嘴里,甜香的汁水,顿时顺着喉咙流入心肺。后来有南方的战友告诉他,那个小果实叫做草莓。“那叫一个甜哪!”父亲微闭着眼,回味着他人生中之一颗草莓的滋味,表情沉醉。
后来,部队发起进攻,在上海外围与敌军对打了12天。1949年5月,上海解放。接着,父亲和他的连队受命开往崇明岛剿匪;之后,又回到上海,执行保卫江湾机场的新任务。那时,17岁的父亲已经成长为一名骁勇善战、智勇双全、不畏牺牲的革命战士。1949年10月25日,经连指导员和班长推荐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
我爱飞行,还没有飞够
转眼到了1950年春节。父亲和他那些经过战斗洗礼的战友们一起,在庆祝胜利的军民文艺大联欢中自编自演了《胜利进军舞》。、昂扬、朝气勃发的舞姿,鼓舞了士气,更踏实了人民群众的心;不仅获得文艺汇演节目一等奖,还荣立集体三等功。
1951年5月,父亲被抽调参加了一次严格的体检。也是那一年的秋天,经过层层选拔,各方面条件均符合标准的父亲,从一千多人当中脱颖而出,由陆军部队输入空军预科总队,乘坐火车北上长春,开始了他的飞行生涯。
一切都是新的。被选拔出的学员们 天南地北的各个部队。那个季节的北方,天气已经萧瑟,父亲看着自己手里从上海提来的凉席,再看看 新疆的学员千里迢迢背来的皮袄皮靴皮褥子,笑了。他们的服装,由一身军绿统一换成了上绿下蓝;日程安排,也被每周一至周五文化知识和飞行理论、周六一整天政治课等等没黑没白的学习填满。
飞行讲义一大堆,机械、电器、特设、气象、飞行学、设计学、领航学、飞机构造原理、空战、截击等等,每一门课都需要运用到计算知识和技能。教员讲述中必须全神贯注,用脑子全部记住——那时候,飞机结构还属于密保;而发给学员的讲义,课后会被放入一个专属木箱中收回,第二天才能重新发下来再看到。所以,想在课后留下讲义复习用是没有可能的。这样的学习,对出身贫苦、只在老家土改时读过两年初小的父亲来说,难度可想而知。我简直无法想象,父亲用了怎样的努力,花费了何等心劲,又度过了多少无休无眠的昼夜,在短短几个月内,拿下了那些堪比天书的课程!他感慨着:“好不容易来了,有多少人想来却来不了,必须用功学会啊!”转而笑说:“我还真是幸运啊,可不是去了的每个人都能学出来的。”1952年1月,根据航校需要,成绩优异的父亲,被输送到五航校的初级训练基地新乡,正式开启了他的飞行模式。
父亲的学员飞行日记。( 提供)
从新乡,到周村,再到济南;从初级,到中级,再到高级……1952年起,父亲每半年转换一个新的训练基地,每个新基地都意味着迈上了更高的台阶。父亲犹记得教员带着他之一次升空时的“感觉飞行”。那次,飞机爬到600公尺高度时,教员提醒他:往下看,看机场。父亲伸头俯瞰,平时训练中使用的偌大一个机场居然变成了那么一小点儿,以至于他开心地笑出了声。后来一次单飞中,他飞到了老家的上空,隔着1000多公尺的距离,看到丝带一样的黄河和小瓢一样的船只,年少时被我的爷爷强按住头祈求的记忆忽然涌上心间。
1953年下半年,在济南张庄机场的高级班训练即将完成时,每个学员都有一个单飞前的考试。这个考试一般由航校的校长、副校长担任考官,跟飞备考学员两个起落,评判是否合格后,才能确定该学员能否放单。轮到父亲,上来的不是校长也不是副校长,却是那个苏联的校长顾问。顾不上许多,心无旁骛的父亲迅速就位。如平常训练时一样,他全神贯注,起飞——转弯——二转弯——三转弯——再转弯,稳稳落地。一个起落完成,父亲按程序走下飞机,举手敬礼报告,等待考官发令后继续完成第二个起落。没想到苏联顾问一句话没说径自走了。一头雾水的父亲愣愣地 在原地,正想着“坏了,也许哪个动作没有到位或者操作不当”,却听到高级班训练中一直带飞自己的那个教员大声喊着:“何子安,快去单飞!”远远地,他都能清楚看到,使劲冲他挥手的教员那一脸兴奋和激动的表情。“我还真是幸运啊,一个起落就成了,什么好事都让我赶上了。”每次说到这段,父亲都掩不住内心的欢喜。
父亲成为了一名空军飞行员。( 提供)
1953年12月,航校学习结束,父亲郑重地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进入空军29师,成为战斗部队里一名空军飞行员。在嘉兴濮院镇,经过短期调配,父亲到了高密。飞着战斗科目的父亲,每天的生活紧张有序。单机,双机——长机和僚机同飞,四机——两个机组,八机——一个大队。父亲一直飞到一级战斗值班——在机翼下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执行战斗任务。直到1956年春天,父亲接受了新的任务离开高密,带着军籍,来到北京,加入中国民航第11飞行大队。
之后,为了祖国建设的需要,父亲于多地辗转,执行各项专业飞行任务。1966年8月29日,原驻北京首都机场的中国民航第11飞行大队(包括飞机、建制以及所有的人员、设备),奉命调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白塔机场,从此内蒙古有了之一支常驻飞行队伍和飞机,父亲也成为内蒙古最早的飞行员。初来乍到,内蒙古恶劣的天气成了之一个考验。当时的冬天,气温达到零下30多度,没有任何经验的父亲,同往常一样想用蘸着机油的布擦拭飞机时,伸进机油桶里的手却一下子被冻住,透亮透亮的,动不了了。基于内蒙古各航 当时极其简陋的基础设施,很多情况下飞机的起飞、降落都存在一定的危险性——比如恰在夜间有了人工降雨的气候条件,而机场却连个跑道灯都没有。机场的老人们都记得,那个当口,各部门的工作人员全体出动,每人提着几盏马灯奔往跑道,隔几十公尺就放一盏,让机组人员识别跑道的大概方位。而飞机起降时巨大的气浪,一转头就把小小的马灯吹得没了踪影……1970年,第11飞行大队奉命转场湖南,留在呼和浩特的一个飞行中队、一个机务分队,组建成民航北京管理局独立飞行中队,父亲担任了副中队长。1977年11月,锡林郭勒盟和乌兰察布盟牧区的11个区县发生罕见的特大雪灾,牧民和牲畜被大雪围困,遵照、国务院指示,内蒙古民航区局派出飞机前往救灾。父亲和他的飞行队伍奉命奔赴之一线,帐篷、斧头、劈柴、粮食……为了准确,他们超低空5米投放。父亲说,他仿都能看到,走出蒙古包的牧民们仰头望向飞机时,神情里掩不住的欣喜、好奇和崇敬。历时138天的救灾飞行,他们成功完成了救灾保畜的任务,为内蒙古通用航空事业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独立飞行中队扩编为民航第24飞行大队,正式划入民航内蒙古区局建制。父亲留在了这个北疆上的首府机场,再没有离开——呼和浩特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他以这里为轴,飞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飞遍了北疆的每一片天空。我见过父亲那只用了几十年的飞行皮包里,整齐地装着厚厚一沓飞行地图,图上红、蓝两色的笔迹标注着父亲飞过的地方,从南到北,从西到东,蛛 般绵密又清晰。仅一张东北地区的图,已经数不过来有多少个我熟悉或者并不知晓的地名。父亲执行过无数次各类不同的任务,飞播草籽、树种、鱼苗,给大面积农田、草木撒药灭虫,为受灾地区空投救援物资,载科学家和探测仪进行地球物理测试,超低空向居民散发防火护林传单,也载着南来北往的旅客飞向各地……他喜欢把每一次的飞行,都当成是之一次——做足准备,才能万无一失。1987年,内蒙古自治区40周年大庆,有个跳伞表演节目,由父亲担任机长,精准把握时速和高度,保证跳伞员们顺利完成表演任务。那天的会场设在大青山根儿,父亲驾驶着他飞了20年的安2飞机,起飞、爬升,至会场上空1500公尺,命放伞员按口令有节奏地解开伞绳。那一天风和日丽,醉人的蓝空中,12名跳伞员从开启的舱门鱼贯而出,安然而错落有致地撑开12张无比鲜艳的大伞,在灿烂的阳光中徐徐而下……那份怡然而又飒爽的美丽,赢得会场上一阵阵浪潮般的欢呼。父亲当然听不到——他已驾着心爱的飞机,雀跃着心情,怡然回返。
记得年少时,几乎每年的春秋两季,父亲都会飞往大小兴安岭执行航空护林任务。回来休整的短暂时日里,他也会把“通火报”的故事讲给我们听。比如在林区上空巡视到火情,会把写在特制纸布上的讯息(火情发生的地点、面积),绑在一只准备好的沙袋上,找有人的地方超低空投放下去。在林区,火灾是每个人的大事,看到绑着警示讯息的沙袋,人们会立刻有组织地进行灭火。那时听父亲讲故事,只觉得好玩儿,却并不知父亲的每一次飞行,其实都提前在脑海里做过许多次精准的模拟。就像那次跳伞,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短短几十秒的成功里,装载了他多少精心的研磨和准备。
父亲飞过9种机型,他能清楚地说出每一个机型的设计工程师那由一大串字母组合的拗口名字。而且他从不觉得,岁数逐年增长的自己,每一次改飞都得从头学习、重新掌握一种飞行技术有多麻烦,反而总是兴致高昂:“我还真是幸运啊,又赶上了技术更新、性能更好的飞机!”
1992年10月1日,60岁的父亲光荣离休。至此,已经安全飞行一万八千多个小时从未发生事故、获得了“特级安全飞行奖章”的父亲,挥别了他心心念念的飞机。可是,又怎么舍得离别?从19岁到60岁,这长达41年的飞行事业,已经深入他的骨髓。他翕动嘴唇,轻轻地说:“我爱这个工作。我喜欢飞行,还没有飞够。”
离休时在白塔机场的留念照。( 提供)
爱一份工作,能到什么份上?我的父亲可以给出让你吃惊的答案。
除了内衣,父亲只有飞行工作服——从上到下,自内而外。几十年过去,白衬衣的袖口、领边早被磨洗得稀碎,却依然洁白如初;蓝色的毛衣底边、腋下早已破损,却又用细密的针脚织补得整整齐齐。每次外出,父亲一定会穿上他的飞行制服外套——衣服的每一粒纽扣上印制的飞机标识都已被磨得平滑透亮;如今已是89岁高龄,寒冬腊月里也还是那一件沉甸甸的飞行毛呢大衣……就好像当年,父亲一直飞到一级战斗值班——在机翼下待命,随时准备起飞执行战斗任务。这一份行头里,仿贮着无尽的能量,让父亲始终葆有蓬勃向上的精气神。
看过父亲的飞行笔记,某年某月某日某个时辰;从某地出发经过某处到达某地;几个架次多少个小时;几时在哪里飞何种机型;天气如何形势怎样;每一天的记录每一月的小结每一年的大结……满满的几大本,文字符号数字图形,一目了然。我惊叹于那一笔一划的认真,父亲说,退下来之后,有了大把的时间,便将这些历史做了详细梳理,以便于日后查询。
父亲获得的特级安全飞行奖章及各种安全飞行奖章。( 提供)
我说,有些事情,我想要写出来。父亲摇头:有什么值得写呢?和我一起战斗过、工作过的战友、同事,已经没有几个活着了。他直视着远方,想了想,忽然笑了:“我还真是幸运啊,今年是我们中国建党100周年,算下来我的党龄都已经72年,到了过去人们说过的‘古来稀’。”
我问父亲,你们打仗的时候,经常没吃没喝,武器也不精良还时有短缺,就没有信心不足的时候?
为什么不足?蒋介石那个运输大队长,什么武器不乖乖给我们送来?父亲斩钉截铁地说:,有办法!
聊这些的时候,我正挽着父亲在家对面的青城公园散步。我们走着聊着,父亲很大声地笑着,以至于感染到周围的一些人,跟着一起笑起来。
父亲说过,他们每一个飞行人员都有三份档案:人事(政治)档案,飞行(工作)档案和体检档案,缺一不可。可我知道,他时时带在身边的,其实是那份独有的“幸运档案”。但,那份档案并不与生俱来,而是父亲懂得,“越努力越幸运”真的可以作为格言;懂得有理想和信念支撑的人才有底气和力量;懂得把滴水之恩当做命运的眷顾;懂得自动滤掉人生中的种种艰难,只在有限的记忆空间存储起这世间一点一滴的美好和温暖。这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和乐观,对生活的热爱和渴望,以及对幸运的认知,在漫长人生的各种琐碎中,是要大智慧来诠释的——我的父亲何其聪慧,他一直认定自己是个幸运的人,并且有一颗懂得诠释幸运的心。
走出公园的大门,父亲还沉浸在之一次在邻近的韩家村,响应号召参军的百十多人集体进餐的回忆中:“那顿饭真热闹,好多人围着一张大桌子,吃得很饱!”我问:“那一顿饭吃的什么可还记得?好吃吗?”父亲朗声应“小米饭。好吃!”接着补充:“是小米干饭。还有汤,汤里面好多的白菜叶子!”
:学习强国
以上就是与1977年蛇的幸运字母相关内容,是关于吉祥数字的分享。看完1977年属蛇的吉祥数字后,希望这对大家有所帮助!